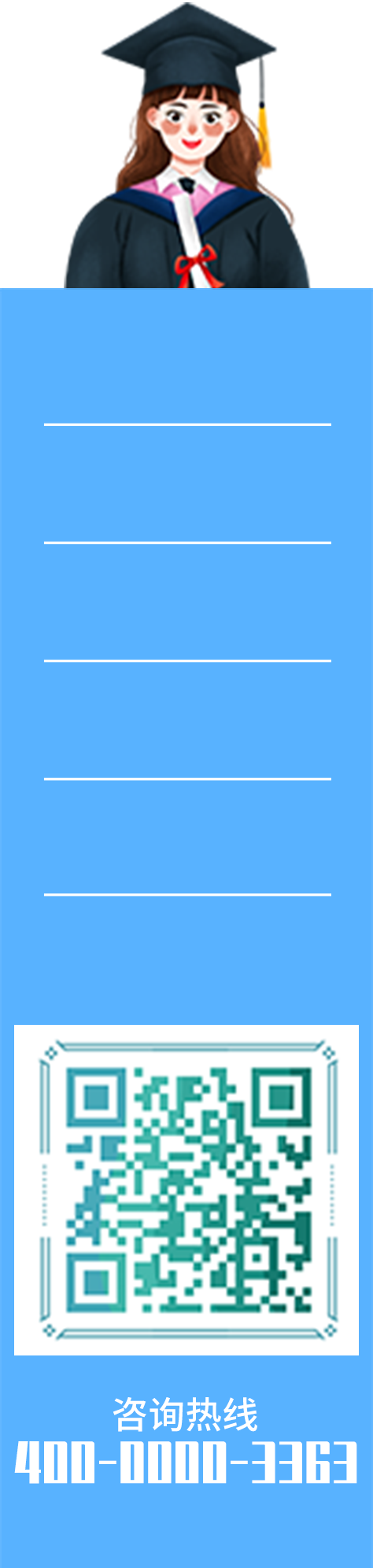深描是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很大程度借鉴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论,“即从被观察的非西方人的角度看西方人自身。”
简单的概括,深描对于社会学研究有如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1.在方法上,深描强调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从而弥补了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盛行的文化主位的缺陷。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转变,瓦解了研究者文化中心主义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更贴近“真相”。
2.在知识获得上,它使得边缘知识进入我们的视域,而这对于理论的不断扩展深入甚至研究范式的转变都具有关键的作用。从研究对象立场出发对事实的理解、释义,所得到的是地方性的个体知识,与那种带着研究者自己的文化意义假设进行的研究,得到的主流知识,有根本上的区别。
3.新的研究视角。深描方法带给社会学研究更多的,特别是在田野调查中,是视角的转换,焦点从研究者转向了被研究的对象,使得整个研究发生了巨变,从资料的收集、整理,直到解读,都力求接近研究对象的主观解释,再靠研究者的思维和语言“翻译”出来。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质疑
虽然深描将文化客位的新视角带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但是它仍然无法摆脱其所阐释的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之分,以及随之而来的认识标准的纠缠。
作为一种文化客位的研究方法,深描强调研究对象的观念和感受,将之作为研究者应该努力去发掘和接近的真知,那么必然使人感到疑惑的是:既然前提是研究对象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是研究的终极目标,那么作为外在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者来说,如何确保自己理解的就是上述可靠的知识呢?换句话说,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我们的认识与他们的想法一致呢?
如果按照韦伯的解释,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得到,一是移情,但这种简单的方法只限于我们彼此都熟悉的情绪和感受;另外就是基于逻辑推理的理解。但是说到底,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经历、背景、组织、文化等等都不熟悉的情况下,韦伯的理解方法就丝毫起不到作用,最终还要依赖我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经历来“主观的”推理,尽管是在对“客观的”收集上来的资料进行的推理。舒茨虽然对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做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区分了主观意义和客观意义,指出我们应该辨别研究者所理解的意义和研究对象赋予行动的意义,但是其宗旨仍旧是不断去接近那种研究对象头脑中的对于行动意义的解释。所以,如何获得这种解释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此,舒茨的对策是:凭借主体间性,通过与研究对象不断的互动,来达到相互的理解。严格参照解释社会学的宗旨来评判,这也是权益之计。在伽达默尔那里,上述问题都不存在,他承认对于行动意义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版本,包括研究对象的和研究者的,而且二者肯定会有区别的,除此之外,行动自身还有独立于研究者及其对象的一个意义,而这种“客观意义”才是我们力争获得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去费尽心思探究研究对象到底是怎么想的。伽达默尔将行动的意义与行动者和观察者分离开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违背了意义的实质——行动的意义是人们主观赋予它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自己和周围环境建构的意义世界里。如此说来,只要我们对异己的行为存有好奇心,就难以逃脱理解它时不得不面临的主体间性的困境。
不论阐释社会学家作何解释,在实证主义者眼里——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中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与实证主义一样,相信确有一种认识方法最能接近真实世界,因而也就同样要面对认识论上的判断标准的诘问。
对此,吉尔茨毫不掩饰自己研究中对文化意义的关注,同时也“承认自己的描述与被描述的对象一样,是一个符号体系、一种文化的解释的人。”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没有“标准”,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文化意义”,充满了个人解释魅力和直觉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因子。
阐释学的说法架空了实证论者的刁难,消极的肢解了认识论的难题,然而这种策略性的方法即使能打消人们对实地研究中的方法论质疑,却无力应对社会学研究中更进一层次的问题,在由经验知识到理论探讨的研究过程中,深描的方法显然不那么适用了。因为,它实际上面临的是从个体上升到集体层面的困难。
抽象共识问题与社会学理论研究
也许,深描这种田野调查方法真正的弱点不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判断标准和理解上的麻烦,而在于当我们借用这种人类学方法从事社会学研究时,要根据由深描获得的资料提炼出社会学理论,从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上升到宏观的总体层面时所面临的困难——在什么抽象层次上存在社会的基本共识。
同类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学中经典的二元论结构:微观与宏观(“所有的象征人类学者都力图展示个人情感与集体表象的辩证关系”)、个性与共性(吉尔茨指出,“人类学者所做的工作正是‘比较不可比较的文化’,在承认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解释话语的自主性的同时,努力寻求人对社会(规范)解释的共同符号媒介。”)。
吉尔茨在他的研究中,试图以“巴厘斗鸡”为例说明他是如何从一个社会的独特行动中抽象出不同社会中的共性和统一性的,“斗鸡表面上只不过是巴厘社会中的一种日常生活之外的特殊场景,……然而它所展示和激发的感受却把‘鸡’、‘男性’、‘赌注’、‘规则’、‘地位’、‘竞争’等巴厘人关注的东西烘托出来,构成一幅生动的几天经验蓝本,不仅把巴厘人的生活趣味一展无遗,而且在隐喻的层面上把憎恶观、乱治观、君臣观也表述的淋漓尽致。”但是,他同时假定了一个关键的前提:即微观生活世界中人们赋予某一行动的意义或者说对某一行动意义的阐释,与统治者从社会总体的、宏观层次赋予这一行动的意义是相同的,至少双方能够达成一个抽象层次的基本共识。当我们试图从个别的资料中提炼出共同的理论或者称作一种理想型时,就需要首先明确这个社会的基本共识,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家国同构”就是清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对于中央政府征税行为的解释,就能够从民间的活动中得到验证性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抽象的共识,就无法从个体行动或者微观秩序层面推演出集体表象或者说宏观结构层面。共识的问题是很多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涂尔干认为,一个社会中不同个体、职业团体各自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虽然不同,但是可以在一个抽象的整体层面上达成道德共识。而共识是维系一个社会的基础。
“通过一个小小的斗鸡场景的文本设置,吉尔茨把我们带到了个人情感与集体表象密切互动的关系当中,迫使我们观看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理想性与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人生观揉成一体的过程。”但问题是,个人在其生活世界中有一套库存知识,用这种知识框架来解释宏观的或者说整体层面的行动,肯定与统治者的解释不同。举例来说,北京浙江村中的人们对政府“治安”、“清理”“整顿”政策的解读是,把它当作一次有名无实的运动,不仅没有影响浙江村人的生意,反而使之在“你追我跑”的游击策略中扩大了生意网络。再看深圳的城中村改造, 1999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于3月5日颁布实施后,明确规定此日期以后所建的违法建筑一律查处,但抢搭“末班车”的心理促使原住民再度疯狂抢建;2002年3月1日,深圳开始实施人大两个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其核心意图便是对1999年3月5日前建设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在进行申报登记,履行查丈、补交地价款等手续后给予合法身份,以达到“既往不咎,不许新建”的目的。本想大赦天下,谁知却又天下大乱,这轮抢建风潮在特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村民的解读是,既然1999年3月5日前的私房可以取得合法身份,为何之后的不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每一次政府下决心整治违法建筑、力图遏制更多违法建筑而出台一项政策,都会引起一次抢建风波!
个体对行动的解释是基于自己生存的环境和习得的习惯风俗,而上层统治者对于行动的解释又是从自己的立场和整个社会的宏观层次出发的,不同的主体对于同一行动的意义的阐释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又凭借什么来从个体的行动来推论集体的表象呢?
小结
由此可见,深描适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策略,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收集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实证主义的认识标准问题可以不被考虑;但社会学不仅仅满足于对现实世界的深描,尽管在问题的提出和阐释中已经充分展现了研究者的个人文化背景和理论观点,但是专业的、纯粹的社会学分析是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也同时必须与实证主义者就认识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立场,这正是社会学中理论探讨阶段的研究与田野调查阶段的区别:一方面,研究者不必掩饰自己的价值关怀,相反应自觉并让其他人知道这一点,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探讨是和经验知识的研究相对独立的,理论探讨永远无法代替事实说话。